- 签证留学 |
- 笔译 |
- 口译
- 求职 |
- 日/韩语 |
- 德语
英语考试课程 德语考试课程 日语考试课程 俄语考试课程 法语考试课程 西语考试课程 韩语考试课程 葡语考试课程 小语种考试语言
英语语法课程 德语语法课程 日语语法课程 俄语语法课程 法语语法课程 西语语法课程 韩语语法课程 葡语语法课程 小语种语法语言
英语口语课程 德语口语课程 日语口语课程 俄语口语课程 法语口语课程 西语口语课程 韩语口语课程 葡语口语课程 小语种口语语言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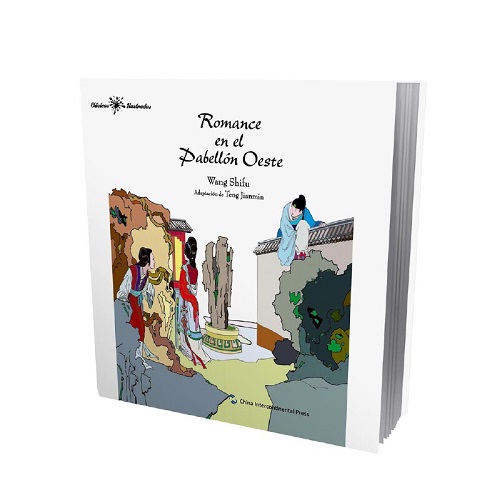
西厢记故事 (西班牙文版) 中国经典名著故事 外语阅读类书籍 正版图书 西语类文学书籍。
【到手价】60.75 元
进口西班牙文版《西厢记故事》(Historia del Pabellón Occidental, Ediciones Siruela, 2021)像一柄来自塞万提斯故乡的折扇——扇骨仍是元稹、王实甫的“待月西厢”,扇面却被格拉纳达的瓷砖釉色重新烧制:月桂代牡丹、吉他代古琴、特雷莎修女的静修院代普救寺的钟声。它不再只是“中国古典爱情”,而被西语世界重新编码为“el amor cortés chino”(中国式宫廷恋),一场发生在唐宋天空下的卡斯蒂利亚幻想。
一、装帧:让“墙”与“门”互换
Siruela 的装帧向来以“纸的建筑”闻名:这次封面用压凹工艺做出一道月洞门,门内却是一片空白——没有张生、没有莺莺,只有一圈金漆像被时间啃噬的壁画。设计者解释说,那道“空门”象征“西厢”本身:它既是偷情的入口,也是伦理的出口;当读者把书翻转九十度,凹洞会变成一堵“墙”,暗示爱情永远发生在墙与门的缝隙里。这种“正负互换”的小机关,把王实甫原剧“围墙”与“越墙”的母题,转译成可触摸的纸面游戏——我第一次发现时,竟下意识伸手去推那道纸门,指尖落空,才哑然失笑:原来“进口”的不只是文字,还有“把东方空间折进西方手掌”的魔术。
二、语言:让“曲”变成“谣”
西译本由阿尔瓦罗·阿方桑(Álvaro Alfansán)操刀,他出身格拉纳达诗人世家,译前立下“三不”原则:不押中原曲韵、不保留科白、不解释典故。于是,王实甫的“碧云天,黄花地”被写成:
“Cielo de jade, tierra de oro,
y entre ambos, un susurro que aprendió a mentir:
‘No es amor, es la brisa de otoño.’”
(玉的天空,金的土地,/ 而两者之间,一声学会了撒谎的耳语:/“这不是爱,是秋风。”)
原文“愁”字被拆成“撒谎的耳语”,瞬间把古典的含蓄转码为西班牙谣曲里“la mentira amorosa”(爱的谎言)传统——在那里,情话本就自带“欺骗”属性,越甜蜜越不可信。张生跳墙一幕,则被处理成“el salto de don Quijote”:他把墙头的莺莺当作“杜尔西内娅”,纵身一跃,却摔进“la realidad que no lee poemas”(不读诗的现实)。这一跌,让“西厢”与“堂吉诃德”共享同一种悲剧性:理想主义者的冲锋,终被平庸地形反讽。
最激进的是“草桥店惊梦”整折被改写成一首十四行诗,十四行内必须完成“入睡—入梦—梦醒—留白”。西语用“soñar”与“desengañar”做押韵,把“惊梦”变成“des-engaño”(拆-欺骗),暗示爱情本身就是一场被语言预先背叛的梦。读到这里,我竟听见深歌歌手的哑嗓子在书页背面咳嗽——原来王实甫的“曲”被阿方桑折成了“谣”,而谣曲的宿命就是:唱完即焚,焚后即空。
三、情节:让“红娘”成为唯一主角
西语版大胆砍掉“老夫人悔婚”“杜将军解围”两条政治线,把全部叙事压进“红娘的听觉”:每章标题都是“红娘听见……”,共十章,像十块声学瓷砖。于是,张生与莺莺的私语、隔墙、焚香、跳墙,全透过红娘的“耳朵”被重新混音——她不再只是“撮合者”,而是“偷听者”“翻译者”“背叛者”三重身份叠加。最后一章,红娘把听来的所有情话写成一封信,投进寺院的焚字炉,火焰却拼出一句西语:
“El amor, cuando se narra, ya es ceniza.”
(爱情,一旦被讲述,已是灰烬。)
至此,王实甫“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”的大团圆,被转译为“爱情只能存在于未被讲述的真空”。西语世界对“幸福结局”的天然不信任,让《西厢记》从喜剧变成“预悲剧”:红娘亲手把“团圆”烧成灰,就像弗拉门戈舞者最后一记跺脚,把欢愉踩成尘土。
四、副文本:让“翻译”成为“注释的迷宫”
书后附了 60 页“反向注释”:阿方桑把王实甫原句、自己的译文、以及译者的“再改写”做成三栏对照,并邀请七位西班牙诗人用母语“二次创作”原句。比如“待月西厢下”被写成:
原中文(拼音)
直译西语(字面)
诗人改写诗(隐喻)
译者再改回中文(二次回译)
四层文本叠印,像一座巴别塔式的“听觉迷宫”。我来回对照,发现“月”被依次译成 luna / lucero / farol apagado / 冷灯笼——最终回译成中文时,“月”已不再是月,而是一盏“被风拧熄的灯笼”。这种“往返耗损”让翻译的“不可修复性”赤裸呈现:西厢的月亮,一旦离开汉语的夜空,就再也回不到原来的亮度。
五、读后:一次“未完成”的握手
掩卷时,我正坐在巴塞罗那地铁 L4 号线,车厢壁的瓷砖与书封面同款钴蓝。对面一位老太太见我读西语“中国戏曲”,好奇地用加泰罗尼亚语问:“结局好吗?”我愣住,只能耸肩:“Depende de qué lengua lo leas.”(取决于你用哪种语言去读。)她笑,下车,留我在车厢里反复咀嚼那句临时敷衍——原来这就是进口西文版最隐秘的赠礼:它让“西厢”不再是一个可以打包带回的东方故事,而成为一面随身携带的“语言镜子”。你越努力用中文去回忆张生与莺莺,镜子里越映出自己嘴唇的陌生——那是一句被西班牙语咬过、却还残留唐诗温度的,未完成之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