- 签证留学 |
- 笔译 |
- 口译
- 求职 |
- 日/韩语 |
- 德语
英语考试课程 德语考试课程 日语考试课程 俄语考试课程 法语考试课程 西语考试课程 韩语考试课程 葡语考试课程 小语种考试语言
英语语法课程 德语语法课程 日语语法课程 俄语语法课程 法语语法课程 西语语法课程 韩语语法课程 葡语语法课程 小语种语法语言
英语口语课程 德语口语课程 日语口语课程 俄语口语课程 法语口语课程 西语口语课程 韩语口语课程 葡语口语课程 小语种口语语言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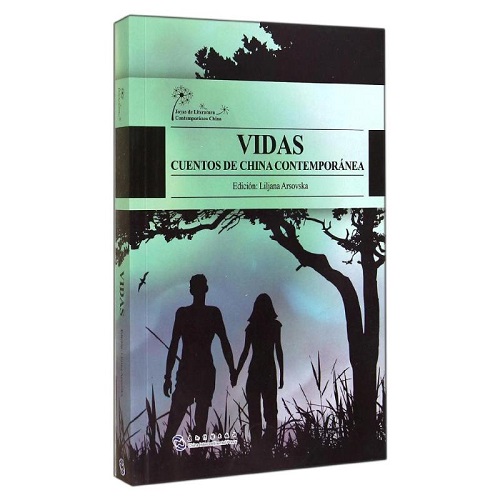
【全新正版】中国当代短篇小说集 (西班牙文版) 外语中国文学类图书 外语阅读书籍 正版图书。
【到手价】52.92 元
把《中国当代短篇小说集》(Antología de relatos breves contemporáneos de China)放进西语世界的书架,就像把一袋刚出锅的麻辣花生倒进桑格利亚酒里——八角、花椒与橙皮、红酒在杯底短兵相接,味蕾先是一愣,随即被一种陌生的热量俘获。这个由五洲传播出版社与巴塞罗那自治大学联袂推出的选本,收入莫言、迟子建、徐则臣、张悦然等12位作家的12篇短制,时间跨度从1995到2020,译者是深耕中国文学二十载的加泰罗尼亚汉学家马诺洛·贝尔塞柳(Manolo Berdeliú)。他这次干脆把“中国”当成一个动词,让高密东北乡的鬼魂与北京的地下室、雪域驯鹿与外卖算法共用一套西语声带,于是读者听见:razón(理性)突然带上了儿化音,corazón(心脏)被一粒孜然烫得发颤。
书一开篇就甩出莫言〈贼指花〉的“鬼叙事”。原文里“手指像偷了油的灯芯”被译成“los dedos como mechas que han bebido aceite de contrabando”,把“偷”换成“走私油”,既保留民间俚味,又让西语读者瞬间联想到地中海沿岸最熟悉的走私场景——拉美煤油、北非汽油。第二段写“我”被女贼捏了一下,指节“火辣辣”,贝尔塞柳没有直译“ardientes”,而是造了一个新词“ají-dolor”,把墨西哥辣椒(ají)嵌进疼痛,于是西班牙读者在皮肤层面“尝到”了中式的辣。这种“本地化微移植”贯穿全书:迟子建〈炖马靴〉里“雪像撒了盐的面案”变成“la nieve es un tabla de amasar donde dios castellano espolvorea sal”,把“上帝”具体成“卡斯蒂利亚上帝”,让安达卢西亚的厨房也落下黑龙江的雪。文字不再只是“翻译”,而是一场“移雪造景”。
莫言提供了“鬼气”,徐则臣的〈摩洛哥王子〉则把“北漂”塞进西语最敏感的社会议题——移民。原文里办假证的小广告被译成“chinoleta——伪造居留的小贴纸”,直接把“chino”(中国人)与“chuleta”(小纸条)杂交,让马德里街头的移民一眼秒懂:原来北京地下室里的“办证”与巴塞罗那地铁里的“假居留”是同一根系。小说结尾,主人公在三元里天桥上把“摩洛哥王子”的护照扔进夜色,西语译文用了一个长句:
“Lo arrojó al aire nocturno, como quien tira la última gota de moro que le quedaba en la sangre.”
(他把它扔进夜空,仿佛扔掉血液里最后一滴摩尔人的残迹。)
“摩尔人”一词在伊比利亚语境里既指中世纪征服者,也暗指今天穿越直布罗陀海峡的北非移民;当“一滴血”的隐喻落地,中国故事突然成了西班牙历史的倒影——原来“漂泊”并不区分肤色,只区分有没有一纸合法身份。
女性视角的文本更见译者的“隐形剪辑”。张悦然〈好事近〉里“月经在高铁马桶里晕开一朵玫瑰”被译成“su menstruación dibujó una rosa en el inodoro del AVE”,把“高铁”精确成西班牙高铁AVE,让本土读者在350公里时速的厕所里也能嗅到血与铁锈。阿乙〈下面,我该干些什么〉那句漫长的独白——“时间像被反复使用的塑料袋”——在西语里变成“el tiempo es una bolsa de plástico que se ha vuelto a utilizar tantas veces que ya no sabe a nadie”,把“不再知道是谁的”改写成“不再尝得出是谁的味道”,让“塑料味”与“人味”混为一谈,既保留阿乙的冷峻,又添了加泰罗尼亚人对于“塑料海水”的环保焦虑。译者像一位潜水员,不断把中文的暗流悄悄注入地中海的洋流,再让两种水域的盐分互相渗透。
当然,选本也有“留白”的噪音:十二篇里八篇写北方,只有一篇真正触及岭南湿热,西南山区完全缺席;科技议题仅停留在“外卖”“高铁”,对算法、直播、短视频几乎缄默。于是“当代”二字被地理与题材悄悄削去一角。但合上书,你会发现这种“片面”恰是选集的修辞策略——它并不兜售“全景中国”,而是把“中国”切成十二枚薄片,像十二道tapas,让西语读者一口一个,辣、咸、酸、甜在舌尖轮播,最后留下一股共同的“后味”:原来在地球另一端,也有人把“孤独”腌成泡菜,把“乡愁”煮成方便面,把“尊严”折成纸飞机扔进拆迁的尘土。至于“中国”是否真实,已不重要;重要的是,马德里凌晨两点的酒吧里,有人因为一篇小说,第一次对一位中国外卖员说“gracias, hermano”(谢谢,兄弟)。
掩卷之际,我翻到书末的“词汇表”——贝尔塞柳把“户口”“编制”“学区房”统统译成加泰罗尼亚语小字注释,像给每颗花椒配上一粒海盐,让读者在麻与咸之间辨认自己生活的倒影。那一刻我突然明白:所谓“中国当代”,并不只属于北京或上海,它也在圣地亚哥·德·孔波斯特拉的火车站、在秘鲁利马的唐人街、在墨西哥城的“中国物流城”;当西语读者把这些故事含在舌底,他们尝到的不仅是遥远东方的味精,更是自己日常里被忽略的苦涩与回甘。短篇集最终完成的,不是中国文学“走出去”的宏大叙事,而是一次“咽下去”的微小动作——让中文的幽灵,借西语的声带,在另一片大陆悄悄打嗝。